当电影《金锁记》被按下了暂停的那一刻,才缓缓地从整出戏中回过神来,耳畔似乎回荡着剧中最后一幕所唱的小曲,和开幕一开始同样的小曲,不过,放在结尾再唱一遍,听起来却是那么的沧桑凄凉,忆起初次听到的当下,比对,心中涌现的只有──苦涩的讽刺和无限的惆怅。
读张爱玲作品就像品一壶陈年老酒,越读越有滋味。每句话像是集结了一身的沧桑所酝酿出来的琼浆玉液。《金锁记》如此,《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亦如此。她总是淡淡的说着,却深深的烙印着。

悲剧的婚姻和价值观
很久之前就读过《金锁记》,看见的曹七巧不过是个豪门怨妇,让积压过久的怨怼与瞋恨给扭曲变了形的一个疯子。年长的时候再审视她,看见的就不只于此,怨妇的背后还有着严肃的婚姻、亲子等阶级议题。
《金锁记》让我们看见古今中外,构成幸福婚姻的必要条件是尊敬。
你必须对伴侣心存敬意,没有尊敬为基础的婚姻,必不圆满。
曹七巧视她软骨病的丈夫如一团烂肉,面对一个需被照顾、终日与床为伍,软趴趴没有生气的肉体,她只有鄙视与憎恨,敬意无从生起。

尽管他家有的是金山银山,还是无法改变她厌倦的事实。现今社会中的豪门婚姻,成功的例子不多,症结在哪里? 缺乏对伴侣的尊敬。豪门婚姻的形态多半是坐拥金银财宝、身份地位的男方,迎娶略逊一筹的美娇娘。
美娇娘对金钱的尊敬,往往多于对男人的品格与学识的崇拜。男人对女人身体的膜拜,又往往多于对她灵魂的渴求。所以豪门的婚姻如同名人的婚姻无法持久,因为两方对彼此的灵魂都没有充足的敬意。

“他们都是恨你的。”“都是恨我的了。你呢,你恨我吗?”
上述两句话,是全出戏我脑中最深刻的对白。
原因,不单只是此段话放于结尾,更精确地说,正是因为放于结尾才显得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最后的提问——是质问?还是自问?我相信曹七巧心底其实早已知道了答案,只是她不想相信,因为,只要一信,自己好不容易才架起的武装就会立即崩塌、瓦解。
她更不能相信,假若一信,不就等于完全否认了一生死命咬紧牙根活过来的自己。

影视剧本里以幻境的方式演出曹七巧的梦,在梦里她得到了梦想中平凡、简单、幸福的生活,梦里小刘日常的生活举动,如 : 结束工作返家、送妻子小礼物,对真实的七巧来说,都像梦一般缥缈而不可及。
以梦境的手法对比七巧的现实生活,和原著以第三人称叙事加上人物对话方式的写作有着很大的不同,原著中读者必须仰赖文字叙述、人物对话、和七巧的待人处事猜测她的心理状态。
但在改编后的剧本中直接了当的呈现了七巧的内心世界,省去了想象的模糊空间,更多的是透过对比手法,让观众了解七巧所生活的环境、所面对的世界、所怨怼的一切,藉由看似平凡的幻境,突显七巧处境的难堪,连最平凡简单的生活都必须借助梦境才能短暂求得。
最后,七巧在面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一生中来来去去的人们对她的恨,最终还是到了梦里,但这一次和剧本开头的梦境却不同,剧本开头的梦对七巧而言是最佳的逃避,是美好的、愉快的,但在剧终时,连小刘都不愿意将这种幸福的幻想延续,以一句“再无瓜葛”彻底粉碎了七巧所希冀的一切。

剧本里的时间过渡长达二、三十年,文字却总是轻轻的带过,仿佛十年的时间在一眨眼间就过去。
对于时间的轻描淡写,就像剧中人物的心理写照,也是现实世界生活的写照。
在生活没有面临巨大改变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着,从不专注于生活的细微变化,直到有天开始回顾时,才发现云鬓染上了雪丝、过去的时间再也回不来。
七巧守着姜家二少爷,求的是解脱的那一日,但等到那一日真正到来后,七巧却没有因此变得更快乐。身体是自由了,不再需要服侍姜家二少爷,但心却还是被那个带刺的曹七巧禁锢着永不得解脱。
小说里形容的七巧「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伤害了身边所有人,只为了替一无所有的自己挣些什么,最后却什么也都没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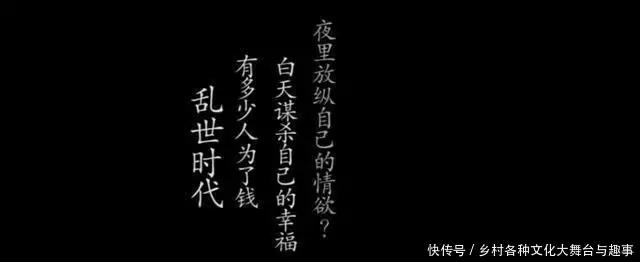
我觉得很妙的一点是——让姜家二少爷从头到尾只以背影出现在舞台上,让观众自行想像二少爷的样貌。从七巧的嫌恶言语,让观众带着朦胧的想像自行塑造这个影响了七巧一生、对她的人生而言极其重要、却又极欲抹去的身影。
还有几个打麻将的场景,将麻将会用到的术语、声音融入唱词中,用唱的来表现麻将洗牌时所发出的撞击的声响。
人物的内心独白也用唱的来表现,小说中只能以第三人称方式叙写的人物内心,在剧本里则能让人物以第一人称唱出心里的想法。唱的速度和曲调上,剧本中提到芝寿的唱调既长且慢,和芝寿在故事尾声中疾病缠身、苟延残喘的生命历程相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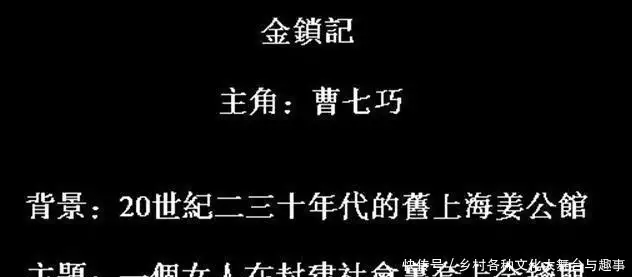
以剧幕情节反衬人物性格
(承接上文戏剧表现来分析)
天伦和乐融融的温馨画面直到丈夫唤了她的名字“七巧”,这时剧情才真正的开始步入主轴。
曹七巧先是一脸疑惑,随后又转为惊恐,以不可置信的神情不停地质问自己的名字,台上光线转暗,直到声音再次出现,灯才又渐渐亮了起来,和先前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氛围,紧张、刁钻、哀怨、悲伤......
突然让人猛然恍悟,原来之前所看到的情景,都只是梦境,假想于曹七巧脑中的美好梦境。

断送了自由,葬送了青春,只能拖着看似美丽的黄金枷锁踽踽于行于豪门大宅内度过痛苦万分的前半生。
等至二爷、老太太死了分家后,曹七巧终于得到了枯等大半辈子而换得的家产。
此时,耳边又响起曹大年所对自己所说的话,什么再委屈也不过三、五年。
回忆和现实交叠,时间比所预想的晚了太多,如花似月的美貌已不再,她已经老了。好不容易从姜家的桎梏挣脱出来了,可是曹七巧却无法摆脱名为金钱的锁链。
分家后的三爷为了骗钱还债而登门到访,三爷满嘴的深情勾起了曹七巧正值花样年华时憧憬却无法获得的爱情渴望,好不容易平定下来的心再次被掀起波涛骇浪,谁料到全部都只是虚情假意,为了骗取自己的钱财而编的甜蜜谎言,他根本不爱她,他之所以会来见她,都只是为了钱。

此后,曹七巧整个人都变了,不再相信任何人,她深信的也只有钱了。
唯有钱,是绝对不会背叛、欺骗她的。她疯了,彻彻底底疯了,为了不要让女儿长安在外到处乱跑让男人给拐跑而打断女儿的脚骨强行绑了小脚,为了不要让儿子长白像以前的三爷流连于窑子决定给其娶个媳妇,如果媳妇压不住,那就花些银两让儿子抽鸦片上瘾留在自己身边,就算变成个无用的废人也没关系,看得到总比看不到好。
如此变态的心理在长白娶了芝寿后也没有片刻的好转,反而更变本加厉,就连儿媳两人的房中闺事也可以拿出来和亲家母摊在麻将桌上说嘴,占有欲如此之强,没事就在家里嘲弄自个儿的媳妇,芝寿最后也撑不住在家所受的精神虐待,病了...
得知长白的姨太太绢儿有喜,怨寂的唱了几句,转过身来对着绢儿像是愤怒又像是疯癫的叫了几声,绢儿一脸惶然连说了好几声不是。芝寿的精神已经崩溃,被这个不正常的家逼到了尽头。长安的心上人前来提亲,做母亲的曹七巧却一口断送女儿的幸福归宿,使得长安往后只能真正的浸于毒品来麻醉自己的伤痛。

很大的妙笔,用曹七巧的幻想来开端,人物的走位和道具摆设的位置有相当有趣、深埋意喻,譬如说姜家二少。
二少所搭配的灯光永远都是昏暗的橘光,毫无生气;
出场的位置永远都在舞台幽暗的一角,而非正中,如二少本身的残疾似的,见不得人,咚咚的木鱼声、低鸣的咳嗽声比声嘶力竭的说话次数来得还要多。
整出戏的过程中不断使用叠影、前后比照、呼应的技巧,尤其中药铺小刘出现的时机点最为关键,最使人省思曹七巧此生一路的选择,再搭配上「金锁记」这三字,其中的讽刺更是让人不胜唏嘘。

深刻的讽刺意象
说了这么多曹七巧缺少的女性自我觉醒,再来说说《金锁记》中那些深刻的讽刺意象。
从《金锁记》可以看见中式教养的犀利。
曹七巧对待子女显得冷酷无情,总猜忌防范着,深怕子女挖走她的财产。
钱是她的命,子女是她的财产,由不得做主。
当女儿长安喜欢上了一个归国学人,她百般阻挠,因为对方曾经有绯闻,又恐他是贪图她家的钱财。当儿子长白娶了媳妇,她惟恐儿子有了媳妇忘了娘,便怂恿儿子整夜吸食鸦片,逼他说出闺房情形,再以不堪的言词,讥笑媳妇种种行为。
最后她逼死了媳妇,也逼退了女儿的如意郎君,换得的是儿女对她的恨。

看似一个变态的母亲,却点出中式亲子关系的意识形态。
中式教养是上对下的掌控,非西方式的民主关爱。诚如《虎妈战歌》中所提到的,传统的中国父母为子女安排好一切,给予严厉的磨练,这是为其将来做准备。
过程中会有责打,但这是为达成目的必要手段。玉不琢不成器,越是磨练越能养成其坚毅不拔的气概。在西方爱的教育的洗礼下,中式教养显的有违人道,甚被贴上虐童的标签。
殊不知中国父母和其子女是一体的,子女的成就就是他们的成就。子女同时是家族的一部分,必须承担传宗接代及延续家族声望的角色。

中国子女从来不是独立于家族的自由个体,他们从生下来就注定要承接父母的期望。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看曹七巧,就知道她的乖戾行为根源为何处。
安排女儿上中学为的是办知识嫁妆;让儿子抽鸦片好管住他,把他留在身边避免去嫖妓赌博,散尽家产;她用尖酸刻薄的言词刺伤女儿,无非是怕头脑单纯的她,人财两失;她爱钱胜过爱子女。
同样的,究竟多少中国父母爱名声胜过爱子女? 说曹七巧虐待子女一点也不为过,说她是中式教养的阴魂亦是恰如其分。

最后从阶级的角度来看曹七巧。
曹七巧是北方的商贾人家嫁入南方的豪门,若非丈夫是个软骨病,恐怕这辈子被唤为少奶奶的机会是微乎其微。
为了这少奶奶的头衔,她损耗半辈子的精力和周遭的姻亲们角力斗争。门当户对的观念深植于传统中国文化中,曹七巧自然是受大户人家鄙视的对象。
妯娌们的冷言冷语、丫环们的暗地非议,自然在她心里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
被排挤的人,总是要想办法生存,于是她慢慢变成言语苛薄、无理取闹的泼妇,动辄搬出她的委屈心酸向人诉苦,也渐渐的无人同情理睬。

而越是无人理睬,她越是变本加厉,发狠的洒泼。
一生斗争下来,伤痕累累,最终就是病痛缠身孤寂而死。社会上充斥许多类似被排挤的人,他们的行为模式和她如出一辙。
先是怨怼,而后攻击伤害他人,其中也包括自己的家人。家暴的男人很多都是在职场上受人排挤的人;混帮派的人很多是在学校受人歧视嘲笑的一群。
于是,曹七巧的语言暴力,以多种形式还魂于现代社会中。
而对自身阶级地位感到自豪的人们,应该读读哈佛大学教授麦克尔·桑德尔所撰写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
古今中外每个社会崇尚的价值是变动的。某个阶层得到高薪受到尊崇,不代表自身的美德或崇高。只能表示这个阶层的人所拥有的才能,在这个特殊的时空有特别的用处,因而得到社会的肯定,所以能享有优渥的生活。
豪门世家的子孙们,大可不必因为出了个会考试或做生意的祖先而洋洋得意,视他人为敝屣。当然,这也是旧时代权贵的“特权”。

戏剧版《金锁记》的人物表达
《金锁记》改编的版本有很多,再从京剧版的《金锁记》来分析曹七巧的人物性格。
戏剧版的《金锁记》,跳脱原著张爱玲精湛的文字意象之描述,而使用了大量现代舞台表演艺术的展现手法。因此,虽然在剧情主轴的发展上没有太大的变动,但是同样的故事使用不同的呈现方式,让观众在欣赏的同时,宛若走入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在戏剧中,场景变换的手法最让人印象深刻,大量使用时空交叠、虚实交错的方式展现时地的流转。有好几段演员都还站在台上,一边唱戏、一边后面就有人来搬动道具布景,等一切配置完整,唱曲也刚好告一段落,几乎是完全没有时间上的延迟、相当流畅地就可以进行下一段了。
也因此整出戏除了上下半场的中场休息之外,整体都贯连得非常精准与紧凑,让人不由自主地看了就停不下来。

而在特殊情节的表现手法上,较特别的是剧中两段打麻将的戏,虽然是类似的动作,但呈现的方式却大有不同。上半场和季泽等人打的麻将是非常具象的,四个人围着一张方桌,翻弄着货真价实的麻将。
而下半场和芝寿母亲等人的牌局,却是以非常抽象的方式进行,没有方桌、没有麻将,甚至四人座位的排列方式都不是面对面地围成一圈,而是肩并着肩、以略微侧斜向观众的方向排成一横列,更由于没有麻将这项道具,因此摸牌的动作可想而知便是用双手直接在空中摸索,配合着演员不时几句“碰”、“胡了”意外地还有几分以假乱真的效果。

而之所以安排用两种差异甚巨的方式来呈现同样是打麻将的戏,实则有它的考究所在。
除了不让重复性太高之外,我想更大的原因是由于两场牌局背后隐含的意义大有不同。
第一场麻将较为单纯,因此表现手法也与一般打麻将的方式没有两样,在此先不赘述。
而第二场牌局则不如表面上打打麻将那般平静,甚至可以说是七巧为了满足个人残忍的私欲而刻意安排的,是充满了城府心机且暗中流泄的。之所以将演员的位子安排成一横排,我想是为了让让观众更一览无遗演员灵活的面部表情及生动的肢体展现,且捕捉角儿们摸牌丢牌的顺序和彼此间的互动,也是一大乐趣。
而打麻将最重要的主角「麻将」这一物件却没有出场,我个人认为是为了让观众能更专注于文词对白的撰述、音调声韵的变化,不至于被麻将的形体和碰撞声响喧宾夺主,忽略了这一重要桥段所要呈现的确切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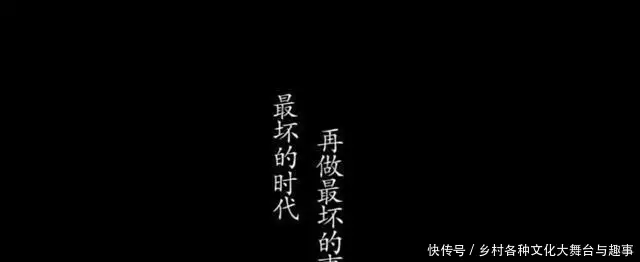
另外灯光的呈现也让人印象深刻,配合着剧情的发展和每一个桥段的主轴,在舞台上运用得相当精准与传神。
其中一段七巧要替长安缠小脚,整个舞台打上极强烈的红光,象征着七巧激烈的情绪与长安血淋淋的痛楚,在愤怒与恐慌之间、在强行逼迫与苦苦哀求之间,巧妙地运用鲜艳的红光做连结,表现出裹小脚的残忍和两人激烈的拉扯。
而为了凸显主角,在七巧和长安身上打上白色聚光,使整个台子不至于因太过艳红而使演员与背景融为一体,也让我们比较能看清两位角儿生动的细部表情。
而在这一段中,同样在颜色上的搭配,除了灯光之外,还有一项相当显眼的道具──裹脚布,不同于传统古代中国所使用的白布,这里七巧拿的是一条长长的、鲜红色的布帛,除了吸引观众的目光外,更加强了血红的意象,效果奇佳。
而另一段抽鸦片的场景,整个舞台上打的是宝蓝色的光,营造出虚幻的景象,配合烟雾的使用,仿佛悠游在梦境中,也是很成功的舞台效果。

另外,音乐的部分亦是相当让人激赏,配合演员唱曲部分的伴奏自是不在话下,另外有许多凸显节奏的打击乐器更是运用的恰到好处。
例如用木鱼、响板的节奏变化来表现人物内心的急切或躁动、用锣或钹或鼓此类的乐器,配合剧情的转折处,加强震撼的效果,往往令人为之一凛,随着演员生动的肢体表现与适时的定格静止,观众也跟着屏气凝神,更加聚精会神地看戏。
而其中最特别的就是七巧与二爷仲泽的一段对戏,卧在躺椅上的二爷,以粗哑的声音嘶吼着,莫大的压迫感充斥全场,让人汗毛直竖,而他手中拿着的木鱼,由他自己敲击,每重重的一次回响,都充分表达出二爷心中的不平与愤怒,再藉由节奏快慢的变化,情绪由缓而急的牵动,巧妙流转,低回不已。

《金锁记》实则是一部旧时代女性缺少自我觉醒意识的回忆录啊。
